大师远去,艺术遗产如何保管
——李可染遗产纠纷案引出的思考
作者:丁一鹤 发布时间:2009-06-13 11:55:47
--------------------------------------------------------------------------------
图为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李可染作品的海报。“实者慧”是李可染的一幅书法作品和一枚篆刻印章的印文,李可染曾解释为:“天下学问惟诚实而勤奋者得之,机巧人难矣。”
李可染先生暮年照片
李可染先生的画作《忽闻蟋蟀鸣》,齐白石题字
李可染先生艺术遗产中的代表作之一《万山红遍丛林尽染》
今年6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而就在一个月前,李可染艺术遗产案刚刚尘埃落定,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大师身后遗产保管问题的关注。
李可染先生于20年前猝然辞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但他留下的艺术遗产却导致了家庭内部持续两年的诉讼。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早在2005年就与北京画院协商筹划李可染作品捐赠以及展览事宜,然而中途由于李可染遗产纠纷案耽搁了捐赠活动,直到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第二天,89岁的邹佩珠就将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件、书法作品122件、速写9册、水彩画13件捐赠给了正在筹建中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李可染艺术馆。
李可染艺术遗产纠纷案并不是个案,在此之前,著名画家王式廓、陈逸飞的后人都陷入旷日持久的遗产纠纷之中,而这就意味着艺术大师的作品将被遗产继承者“瓜分”,必然造成大师作品的支离破碎。艺术大师身后的艺术遗产到底该如何保管,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很多艺术遗产的矛盾和争端,首先可以从艺术家本人那里得到有效控制,生前订立遗嘱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很多艺术家都觉得立遗嘱“不吉利”,而且伤及家庭和睦。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误区。
其次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收藏管理机制,如黄宾虹在生前就将大量作品捐赠给国立博物馆。后代子女在继承艺术品遗产时的做法无非两种:一是由家族共同继承并组建基金会,二是由家人捐赠建设艺术家个人纪念馆。但这两种途径都有一定的局限:家族管理难以保证保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且家人想法难以统一,一旦出现分歧就容易闹上法庭;而建设纪念馆,则要面对盖馆容易养馆难等资金困难。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于大师级艺术家,在其去世时就应该由其家属子女、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政府机构三方力量组成对其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专门机构,对遗产进行共同保护。如果艺术家的遗产保护能上升到立法层面,将是一条正确出路。
事件回放
谁动了李可染的遗作
李可染先生1907年3月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平民家庭,先后入上海美专师范科、杭州西湖国立艺专研究生班,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后经徐悲鸿介绍师从齐白石,白石老人称其为“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
在李可染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赢得了两位同样具有很高艺术天赋的女性的爱情,两位夫人先后为他生下了7个子女。
李可染与第一任妻子苏娥于1931年结婚。1938年8月,苏娥死于伤寒症,年仅29岁。苏娥为李可染生下1个女儿3个儿子:李玉琴、李玉双、李秀彬、苏玉虎,由其父苏少卿抚养长大。
李可染的第二任妻子邹佩珠是李可染妹妹李畹的同学加好友。1944年1月,邹佩珠在重庆嫁给李可染。婚后,邹佩珠为李可染生下了2个儿子1个女儿:李小可、李庚、李珠。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邹佩珠也担任中央美院教授。这个时期,李可染的艺术创作进入高峰期,先后创作了大量的传世名作。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猝然辞世,留下大量的绘画精品和藏品,但没有留下遗言,更没有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分割,由此引发了日后他的至爱亲人间的一场长达两年的遗产官司。
1991年2月21日,李可染的遗孀邹佩珠及2个子女(李庚当时在日本,表示放弃继承权),和苏娥所生的4个子女坐到了一起,讨论李可染的遗产处理问题。
这次家庭会议由邹佩珠主持,就李可染艺术的发扬及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商讨,并形成《一九九一年春节家庭主要成员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有:为了弘扬李可染的艺术,完成其遗愿,大家同意将遗作中的精品和代表作集中保管,作为家庭成员的共同财富,以备将来提供给纪念馆、出画册、巡回展览、复制宣传等使用;将于适当的时机(大约10年左右)奉献给国家;在遗作中划出一部分作品给“艺术基金会”和“家庭基金会”使用。
1991年11月13日,李可染的继承人共同签署了《李可染遗产继承问题协议书》,约定:以李可染艺术发扬光大为前提,继承人按继承法的规定享有继承权;李可染的主要遗产是绘画和书法作品,要进行清点;集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由邹佩珠统一保管5年;拟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和“家庭基金会”;给子女每人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两张,一般的四张,书法作品二至三张。
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各子女分得李可染遗留的部分作品。据邹佩珠的回忆,李玉琴、李玉双、苏玉虎、李小可、李珠分别分得16幅绘画作品,李秀彬分得17幅绘画作品,李庚分得4幅绘画作品。
除去子女们已经分掉的作品,李可染还有多少艺术遗产呢?按照原告李玉琴在起诉书中所称:1989年末,双方一起对父亲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清点,共500余幅,而1992年再次清点时约有400多幅,当时邹佩珠还从画室里拿出了李可染创作的10幅超大型山水画作,让各当事人开眼界。而按照邹佩珠的说法,李可染的绘画作品仅存317幅,这还包括已经分给子女的那部分。
在此后的岁月里,苏娥所生4个子女发现“邹佩珠及弟弟李小可根本不征得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擅自处分家父的作品,经常被拍卖或赠送。李可染基金会存在账目不清、暗箱操作的种种问题”。
与此同时,李可染作品在新世纪以来的拍卖价格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价:2004年《井冈山》以1100万元成交;2006年《漓江天下景》以1350万元成交;而到了2008年,李可染的代表作《万山红遍丛林尽染》则拍出4000多万元的天价。
于是,在2005年和2006年,苏娥所生4个子女多次向邹佩珠提出析产要求,但这会使李可染的作品无法保持完整性,遭到邹佩珠的拒绝。
李可染到底画了多少画
2007年4月,李可染的子女们坐在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李玉琴、李玉双、苏玉虎作为原告,提出分割李可染遗留绘画作品881幅、书法作品463幅、收藏作品139幅、水彩作品25张、印章189枚、素描18册978幅。而李秀彬要求将未入册的10幅超大型山水画作,作为遗产进行析产继承。
在法庭上,被告邹佩珠主张李可染遗留中国画绘画作品317幅(其中已由子女分得101幅)、书法作品312幅、印章180枚、水彩作品25幅、收藏作品91幅、素描共9册973幅。
除了由子女分掉的101幅绘画作品,2007年2月12日,邹佩珠与北京市文化局签订《托管协议》,约定将李可染的部分作品交由北京市文化局托管。在法庭上,邹佩珠称托管物品的唯一用途是待李可染美术馆建成后由美术馆收藏,并主张托管的作品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中所析出的归其个人所有的那部分。
除了子女分掉的101幅绘画,邹佩珠托管的108幅绘画,还有就是更引起双方争议的一部分作品,包括为筹集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基金,为李可染办丧事等各种活动,共处分了31幅作品。
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李可染的艺术遗产中到底有多少作品。仅就绘画作品而言,原告主张有881幅,而被告主张只有317幅,双方对遗产的数量分歧较大。
对于邹佩珠在法庭上提供的李可染的遗作清单,苏娥所生子女显然不认可。他们认为,李可染13岁学画,82岁去世,根据他们的查证,应该在2000张到4000张之间。
邹佩珠解释说,李可染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而且,李可染作画很慢,其口头禅是“废画三千”。邹佩珠还透露了李可染作品许多不为人知的去向:李可染是一个生活上需要别人认真呵护的人,他经常丢失作品,比如带着很多的画去美院给学生讲课,讲完课坐公共汽车回来之后就发现画不见了。在画界,自古以来就有作画送人的传统,李可染送什么人、送多少幅画、送什么画,她都是不知道的。建国以后,李可染遵照政府的指令,给国际友人或有关单位作画,这些画作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可染。
2008年11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依法确认李可染遗留绘画作品308幅,其中各子女已经分得绘画作品92幅,由邹佩珠托管绘画作品108幅、保管绘画作品108幅。其他作品,法院核实为书法324幅,收藏91幅,水彩25幅,素描16册973幅,印章175枚。
法院依法分割李可染遗留的绘画作品共计308幅。首先,应当由邹佩珠分得154幅,其中包括邹佩珠托管的108幅绘画作品。其余的154幅绘画,先刨除应由李庚继承的9幅,剩余的145幅绘画,李可染前妻子女共分得73幅;邹佩珠及子女共分得72幅。对于收藏、水彩、印章、素描、书法作品,法院也按照继承法的原则进行了析产。其中,法院考虑到175枚印章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并且印章分散之后,可能会对李可染作品带来不利影响,法院将175枚印章判归邹佩珠所有,但将邹佩珠保管的190幅书法作品判归李玉琴、李玉双、李秀彬、苏玉虎所有。
一审判决后,双方都对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2009月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法院最终认定李可染绘画作品为308幅。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件、书法作品122件、速描9册、水彩画13件归遗孀邹佩珠所有。
2009年6月1日,“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李可染中国画作品108件、水彩画作品13件,涵盖了李可染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精品,既有李可染早年创作的《天王送子图》、《卖唱图》等经典人物画作品,也有奠定其山水画巨匠地位的代表作品《雨中漓江》、《万山红遍丛林尽染》等。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张硕的人物生平
捐赠是李可染的意愿
2009年6月1日,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展出了捐赠的著名画家,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幅山水画、122幅书法作品、13幅水彩作品、9册素描作品、45幅收藏作品。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在作品集的前言《令人感佩的义举》中说:邹先生捐赠的这批李可染作品能完全反映李可染的艺术辉煌历程和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可以设想,后人通过这批作品将获得学习上的宝贵机会,并进而学习李可染先生对于艺术永无止境的而又朴素赤诚的求索、创造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此前的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媒体倍加关注的李可染先生遗产案作出终审判决,此次捐赠的就是法院认定的属于邹佩珠的作品。
李可染先生遗产案终于尘埃落定。
日前,邹佩珠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首次开口谈了前一阶段媒体关注的一些“家事”。
关于这次捐赠,邹佩珠说,捐赠作品给国家是李可染的意愿,也是我们二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邹佩珠说,在40年代初,李可染立志要改革中国画,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得以弘扬,并想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做一点事。这也是李可染与我两个目睹、经历20世纪所有苦难的文化人共同立下的志愿。为此我们奋斗一生,从未改变。40年代李可染提出“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此后李可染不顾一切地向目标进发。我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负担,为家庭生计做兼职,一个人做多份工作,后期又放弃自己已有成就的雕塑事业。
这次捐赠的作品均为李可染先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整体代表李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邹佩珠说,李可染精心将一生各个时期的作品保留,晚年还用价格较高的晚期作品换回自己早年作品,他是为了保留完整的系列,目的是要将一生的研究成果交给国家、留给后人。生前他多次说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像乒乓球一样为国争光。那时作品价格不高,他不敢想建美术馆的事,加上1989年他是猝死,所以没有安排好这件事。
团结孩子们一起捐赠
李可染有过两次婚姻7个子女,邹佩珠说,可染去世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团结全家办好捐赠这件事,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可染在世时工作忙,怕打扰,前妻的几个孩子回来的很少。但他去世后,我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能来的都叫他们回来,不管在哪有活动都是全家一起去,不能都去的也要派代表。丧事办完后,我给每个孩子(七个)每人拿出一摞存单,因为那时可染刚刚有稿费,有点钱了我就分着给存,每张有50元的,100元的。数额是按照每个人生活情况不同存的。比如老大李玉双困难、李珠困难,给他们各存了15000元。李庚和李小可是画家,生活比较好,给他们每人只存了5000元。其他孩子1万元左右。当时大孩子们很感动。那时可染作品的价格并没有多少钱,山水价格稍微多一些,哪有现在他们给我算的动不动就上亿的账。
邹佩珠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留在家里作品的意义,刚开始他们没有说要分画,只是说:“妈妈给我们一些作品留作纪念。”这样我就从他们爸爸的各种画中,包括我们的收藏品和书法中,各拿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给了他们。后他们又几次提出,我也了解他们的生活需要,那时也卖不了太多钱。有的孩子上学需要;有的要买房子,这样我也就同意了。先后分四次,每人共拿走16张作品和部分书法作品及少量收藏品。后来在诉讼中他们只有一个人承认16张,其他人都没有承认这么多张。虽然已拿走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作品,我还是希望团结他们一起捐赠,因为要让可染高兴,放心。要让社会觉得可染的孩子与其他的不同,在可染去世后的十六七年里,家里感情我认为一直很好。
价格暴涨带来的变化
2005年下半年,国家经济大好,中国画价格暴涨,邹佩珠说,可染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想法不同了,对以前的约定产生变化。真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邹佩珠原计划是在2007年可染百周年纪念时把他的作品捐献出来,给李可染百岁送个礼。但就在李可染百周年纪念日前的2007年四、五月间她接到了李可染前妻子女的起诉书。在长达两年的诉讼过程中,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敏感问题:李可染过世后的作品流向和卖画收入。
邹佩珠说,李可染是个画家,以绘画为生。一生为生活、为友谊、为国家或各种原因,生前他卖的、送的和专门创作或是其他原因出去的画,早已不是我们家的,更不属于李可染的遗产。说多少作品不翼而飞,是不真实的。再说按照法律规定,可染留下的所有作品,我有9/16,其余七个孩子每人仅有1/16。也就是说我要是保管员也保管的是我自己的,弄“飞”的也是我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和可染一辈子的心血,是我在多少次灾难中用命保存下来的。为的是要展示出来给后人看,我怎么能让它们“飞”呢?
另外,他们说几十张作品我擅自卖了一个亿、几个亿的,媒体也不停地出来炒,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画能值几个钱?当时可染过世后,我带领全家给可染徐州老家为他修建的李可染旧居捐了十张绘画作品和10张书法,全家都去了;他们要办家庭基金会,拿了11张山水画,后因种种原因倒闭了,每人分了几万块钱;捐给中南海、故宫、统战部、江苏省美术馆等一些国家机构部分画作,他们都知道并参加了大部分活动;一些可染生前答应给的画,比如陈香梅原本可染约她是12月5日下午来,可染上午去世的;像京丰宾馆他们派司机给可染开了两年车,可染答应给两张画;等等。如此这些,后来我都按可染的意愿,把画给了。还有就是为办丧事、购买、修建墓地、成立基金会、办展览、为给可染出书等出售过一些画。可染过世后办过近20次展览,出版过几十本书,也就是通过这些展览和出版的画册,社会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肯定可染,可染的作品才有今天的价值。我的原则是,把可染创造的财富用于发展他的事业、达到他的目标,作为他的亲人,是不应该有任何异议的。17年中大家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过异议,也都知道并参与了大部分活动。
我对李可染有了交待
邹佩珠说,这次捐赠的只是法院判给我的作品的一大部分。我也正在同中国美术馆谈,建立李可染专馆,我会再从剩余部分中,捐赠一些作品。他们同我的根本分歧是,他们要把作品卖了,达到所谓的“双赢”。我不同意,我不要双赢,我的东西就是要捐给国家,留给历史和后人。
邹佩珠说,原本家务事也不想谈,想给可染减少不好的影响。可染的前妻是1938年去世的,1943年我和可染相识,那时他是个一无所有浑身是病的穷教书匠,只有四个孩子。今天所有的一切是我们两个共同创造得来的。我们两人一起定下目标,共同努力,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生活,承受了所有苦难。我们一同经历了战争、自然灾害、多次政治运动、疾病痛苦,这一辈子我只能用“提心吊胆”来形容。可染去世的20年里,由我主持他的事业,把所有财力、精力和各种社会资源,都用在可染艺术的宣传和研究上。这个开销很大,但我从没有心疼过。而我个人的生活,在他过世后的20年里没有任何改变。同以前一样,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不是为了李可染的事业,我绝舍不得卖一张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远不如一般人。
家务事实在不想讲,说来说去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更伤李可染的心。今天我不得不讲,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嫁到李家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从没有过一段安宁的日子,回想这些,我内心很痛苦。再过一个多月我就90岁了,今天我已基本完成了李可染和我的愿望,我可以对李可染有个交待了。其他毁誉对我这个耄耋老人来说已经不重要,只是希望他们能走好自己的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生灵涂炭,使他的心激荡不平,再也无心当教书先生。
1938年春,他满怀救国之心返回故里,投笔从戎,参加了德县教育界人士李玉双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同年10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乐陵举办军政学校,遂前往学习。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结业后留校工作。
1940年后,历任平禹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冀鲁边二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兼专署干训班指导员、副校长等职。
1943年1月,任中共德县工委委员、德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虽被敌人两次抄家,家人逃散,要饭为生,但他仍毅然表现出恩义待仇的风度,以国事为重,团结抗日力量,正确执行上级党的翻边战术原则,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将县的活动中心由东部农村转移到接近德州城的六、七区一带的农村,坚持和发展了德县抗日根据地。身为县长,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周围群众。他率县大队在一个地方住下后,群众常敛些干粮给同志们送来,送来的干粮各式各样,他总是挑最差的吃。群众感叹地说:***的县长就是同旧县长不一样。
1943年农历8月15日,冀鲁边二地委派遣他进入济南市,领导“青年抗日联盟”,开展济南党的地下工作。他以青岛《新民报》社济南分社记者、税卡职员的身份做掩护,化名王振亚,忠心为党工作,争取和团结了二、三十名同情我党工作的积极分子,并成立了“敌工组”,设立了“洛口联络站”等地下秘密组织。
本文来自作者[访客]投稿,不代表汇盛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hs59.cn/hs/337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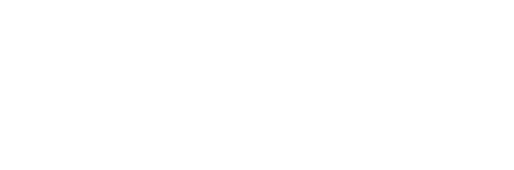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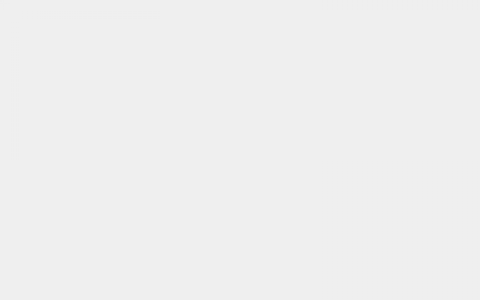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汇盛号的签约作者“访客”!
希望本篇文章《如何记成前人的艺术遗产》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汇盛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大师远去,艺术遗产如何保管——李可染遗产纠纷案引出的思考作者:丁一鹤 发布时间:2009-06-13 11:55:47----------------------------...